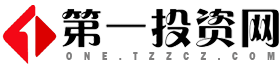一个人的诗歌长城——陈尚君先生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编辑出版轶事
《唐五代诗全编》,一座雄伟的唐诗长城!
记得十二年前,唐代文学专家、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先生前来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272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,看望过社领导后来到我们编辑室,我搬出一把民国木制绿皮面折椅打开让他坐,他那魁梧的身体坐在偏小的椅子上有点不太合适,但他毫不在意,调整好坐姿后就和我们侃侃而谈自己正在开展的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编纂工作,两眼放着光。记得他说他的电脑里建有一万多个文件夹,我当时被惊到了:这样一部巨编仅靠一个人来做,要干到几时啊?!
八年后,当陈尚君老师再次来到我社,我们已经搬迁到闵行区号景路159弄世纪出版园。他陆续交齐了《唐五代诗全编》的全部书稿。陈老师凭着勇气、智慧、勤奋和毅力,也凭着他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竟然单枪匹马跑完了这场学术“马拉松”。虽说只是一个人的长跑,但他毫不孤独寂寞,因为一路上有数千位唐代诗人、古今学人的陪伴和跨时空交流,不断有新的发现,令他激动和兴奋;当然还有贤内助孔沂澜老师的一路相随、悉心照料,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,使他可以全身心地迈开步伐。

早在康熙年间,十位翰林院学士花一年半时间编成《全唐诗》,由于时间仓促,所采之诗主要取自明末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和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,故缺漏讹误俯拾皆是。陈老师新编《唐五代诗全编》有一个宗旨,就是要让唐诗回到唐朝,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陈老师充分利用互联网、数据库,对现存的每一首唐诗的所有版本进行汇总研究和校勘,以那些较早的版本作为底本和主要参校本,再校以后来的各种版本,厘定出一个最接近唐代诗人原作的正本。故新编内大部分诗歌的标题和诗句内都有许多校记,诗尾则罗列了该诗的各种有价值的版本。陈老师说,他是竭泽而渔,穷尽了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资料。甚至那些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、某些小城小报上一些有关唐诗的“豆腐干块”的小文章,他都不会放过。
陈老师说,他爬梳文献时常常觉得自己是在抓特务,每当发现一条新线索时都会特别兴奋,兴奋之余,不得不仔细考辨一番,既怕遗漏一个特务,又怕制造一起冤案。每天都在这样的兴奋与紧张之中,一点也不觉得苦累,反而乐在其中。陈老师又自比为唐朝户籍警,他对大部分诗人的籍贯、家世、履历、交友、作品版本以及奇闻轶事,都烂熟于心。因此他能在编完一位著名诗人的诗作后,把他亲朋好友的作品附于其后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。
《全唐诗》共收作者2500余人,诗49000余首,其中重收、误收、伪作的数量十分庞大,有问题的诗歌数当在6000首以上,陈老师一一为之考订,将疑伪诗一一备录于该人的“存目诗”之下。《唐五代诗全编》共50册,收作者4200余人,收诗达55000余首。
四年前,陈老师陆续将书稿交给我们出版社,社领导非常重视,文学编辑室抽调了超半数骨干组建《全编》编辑团队。
我们这个编辑团队的编辑,老中青都有,可谓各有所长,彼此配合默契。比如年轻编辑戎默,悟性极高,当大家还没有弄明白陈老师的体例时,他已经完全摸清楚了。有什么疑难,大家都喜欢问他。他业余爱好拳击,出拳迅猛,干起事来也很投入、很利索。《全编》出版前三个月,他几乎每个双休日都来单位加班做二审。他还负责与排版厂对接和全书统稿工作,故对《全编》的出版贡献尤大。
中年编辑常德荣,学识渊博,藏而不露,是标准的“老黄牛”。他偶然在乾隆《安溪县志》中发现詹敦仁、詹琲父子的5首佚诗,提交给陈老师,获得了采纳。年轻编辑张卫香做事极其严谨,心细如发,在所审稿件上批改得最多。她不光认真核对底本,在全书体例上也力求统一。有一次陈老师来社里和我们编辑交流答疑,开玩笑说:“看卫香看过的稿件,我总是战战兢兢,像小学生看老师批改过的作业一样。”又说他认真对待她提出的每一个疑问。另一位年轻编辑彭华,头脑灵活反应快,善于变通,对于稿件内出现的体例问题,往往能提出较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。老编辑黄亚卓虽然最后加入审稿行列,但也认真负责,能按时圆满完成任务。
我是《全编》编辑团队中年龄最长的,早年对佛教比较感兴趣,责编过“佛学名著丛刊”,读过一些佛教经典,还曾校点、注释过《金刚经》和《坛经》,对于佛经的行文习惯、佛教名词术语等都比较熟悉,故《全编》中僧人的诗歌我审阅最多。印象最深的是审阅释宗密的诗集。
我发现宗密集内有很多偈诗很长,根据大小标题判断,应该是一组偈诗,而非一首。可能因为陈老师依据的底本排成了一首,所以都没有分段。我根据原经文、大小标题的题意来判断是否要给长诗分段、分几首,大多为陈老师所采纳。这个工作看似简单,实则我要读懂佛经、仔细揣摩大小标题相关联的意思才行。为此,这部分内容我细细审了两遍。等校样排出来后我再审,又发现最后部分有不少标题的层级混乱,一查佛经原文,发觉好多是一组诗,上面应该加一个大标题来统摄才行。因为原来佛经底本上没有标题,我就按照经文内容来拟,一共拟了10条标题。虽然费了很大力气,但颇为得意,就在校样上随手批道:“所拟标题均取自经文,非胡编也,有充分信心,呵呵。”陈老师看后批道:“当然充分相信!!!”他对我拟的标题一字未改。我倒没觉得自己有啥了不起,就感觉只要你能尽力提高书稿质量,编辑和作者之间是可以达成高度信任的。
至于改正偈诗和讲经文、变文内诗歌的一些错别字,那是经常的事,因为底本《大正藏》《续藏经》和敦煌写本原来就存在不少讹误。这里不多说,只举一个好玩的例子:《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唱辞》七、八两句为“四脚距地而起,喷(口孫)嚂?而云非”。按,第四句作“路见两牛相觝”,是说两头牛相斗,那么这两句说的应该也是牛。此诗前七句都是六字句,到了第八句突然变为七字句,读来很拗口,显然不符合古诗韵律,且“云非”两字完全不通。我苦思冥想后恍然大悟:应该是“飛”(“飞”的繁体)字。按,“飛”字的草书有点像“云非”两字上下相连,故敦煌文献整理者误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了。如作“喷(口孫)嚂?而飞”,则和“四脚距地而起”意思相连贯了:四只脚离开地面,不就是飞吗?陈老师看后完全赞同,说:“能这样真不易!”
经过我们编辑团队四年的努力,《全编》终于出版了。陈老师花费40余年光阴,砌起了这座雄伟无比、可以屹立久远的唐诗长城!而我们编辑只是做了少许修饰。陈老师曾经用孟浩然的两句诗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”来形容对唐诗的整理和欣赏,我相信他独力建造的这座诗歌长城,一定会吸引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们前来登临观览。
声明:本网转发此文章,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,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、消费建议。文章事实如有疑问,请与有关方核实,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,仅供读者参考。